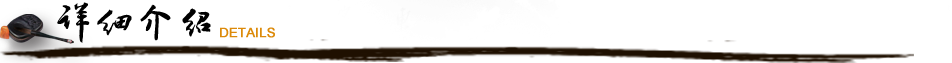
《新快报》王世国:文化修养不能决定书法水平
2020年7月4日,《新快报》“收藏周刊” 发表《王世国:文化修养不能决定书法水平》,现抄录如下,供大家讨论。
王岳川先生曾在《学习时报》上撰文《文化有多深,书法就有多高》,批评当代书法“先锋”们跟随百年前的西方而大谈形式主义;倡导书法应当回归中华传统文化和具有“正大”气象。文中一些观点具有积极意义,我也赞同。不过,阅罢全文可以知道,他所说的“文化”就是与西方文化相对的中华传统文化,特别是“先秦诸子、孔孟老庄、唐诗宋词及名言警句”等“历代的经典”;并以此作为书法不可或缺的“含义深蕴的内容。”
他这么说,显然欠妥。诚然,书法家必须有文化,而且其文化修养和文化底蕴的深度,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书法艺术的高度;但是,由此得出结论——“文化有多深,书法就有多高”,这就错了。因为,文化底蕴深厚,其书法未必高超高妙;文化与书法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,两者之间并非因果关系;更何况“文化”内涵深广,书法家的文化底蕴应当包括世界所有的先进文化,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华传统文化——“历代的经典”。可惜,执这种错误观点的在当今书坛大有人在。
文化深的人其书法就真的高吗?那不一定,一些人文化深,其书法水平并不高。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的《四库全书》总纂修官、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纪晓岚,其学问和文化修养可谓高深。可是,他书法水平并不高,其书法虽有一定功力,但是写得循规蹈矩,四平八稳,缺乏性情和神采。对此,他自己也十分清楚,从不以书法家自居。他曾写下两首诗自嘲道:
“笔札匆匆总似忙,晦翁原自笑钟王。老夫今已头如雪,恕我涂鸦亦未妨。”
“虽云老眼尚无花,其奈疏慵日有加。寄语清河张彦远,此翁原不入书家。”
他还把这两首诗刻在案头的砚匣上,用以自省。纪晓岚到底是一个明白人,知道自己因为没有时间临习“钟王”法帖,以至于功力不足的短处,戏称自己写的字只是“涂鸦”而已,算不得书法。
像纪晓岚这样有自知自明的学者和文化人并不多见,更多的是以文化欺负人。有的人自持有学问,在书坛上有话语权,或者掌握着专业媒体,于是便指点江山。明明那字写得毫无生气、不过是“馆阁体”或书生字,也要大赞“高妙”;明明横涂竖抹,笔法拙劣,也要大夸“创新”。由此可见,书法家要有文化,文化修养高深的确有助提高他的精神境界,并对其书法的格调气韵产生积极影响。然而,书法毕竟是书法,它不是简单的写毛笔字或文字抄写;书法要临习经典碑帖,专门训练;创作时要遵循艺术规律和书法的审美标准。书法家高深的文化修养,需要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完美地表现出来;况且对书法艺术形式的追求并不就是低下,就是形式主义,“技” 一样可以近乎 “道”。
书法家毕竟是要靠作品说话,是要用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,才能证明自己在书坛或书史上的地位。盛唐时,湖南乡下的和尚怀素并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,甚至吃肉喝酒,不守清规戒律,但是他那骤雨旋风般的狂草却震动书坛,誉满天下,得到了社会名流承认和赞扬,成为一代大家。清代邓石如,一介布衣,也不见有著作传世,文化修养并不高深,可是他的篆隶书法,深沉雄健,苍古质朴,上承绝学,下开新风,成为清代书坛上的一座丰碑。在书法史上,如此文化不深,但其书法却很高妙的书法家,多不胜数。因为,艺术之事主要是靠艺术家天赋的性情,以及勤奋学习而得到功力,这就是明代书法家祝枝山所说的“功性两见”。而文化修养的深厚与否,并不是其艺术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。东汉张芝正是靠着他的天赋与勤奋,临池习书,池水尽墨,而成为“草圣”。
